
《深度对话》完全版>>> 腾讯深度>>>

中学教科书上有不少内容都和学界的研究成果背道而驰,一些基本史料或史实存在着严重的错误。这也就难怪,不少中学生进入大学重新学习历史之后,会产生很大的颠覆感
人物:杨奎松 对话者:白伟志 编辑:杨余 统筹:vingie【我有话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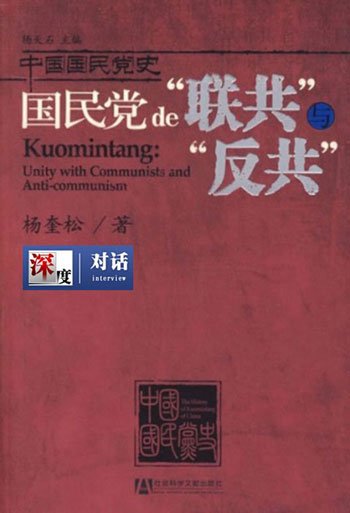
中国的历史教育比较失败
深度对话:最近“袁腾飞事件”炒的沸沸扬扬,不知道你怎样看待袁腾飞式的历史老师了?
杨奎松:我对袁不了解,也没有读过他的东西。
深度对话:你觉得现在学生所接受到的历史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理想中的历史课是怎样的?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改善现状?
杨奎松:我曾经给一些中学老师讲过我的感受,那就是,中学的历史教育多数情况下实在是比较失败。
尤其是近现代史的知识传授,多半并不是在传授知识和方法,而是在逼着学生死记硬背一些政治观点和教条,以应付考试。
结果是,造成许多从小喜好历史的同学对历史产生厌恶感,所背之物很快就丢到爪洼国里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的进步突飞猛进,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中学教科书上有不少内容都和学界的研究成果背道而驰,一些基本史料或史实存在着严重的错误。
这也就难怪,不少中学生进入大学重新学习历史之后,会产生很大的颠覆感。这种情况在目前这种应试教育和现行考试制度下,恐怕很难有所改变。

新书《“中间地带”的革命》讲解“中共成功之道”
深度对话:祝贺您的新书《“中间地带”的革命》的出版,学界不少人士已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们都知道,这本书是在1991年《“中间地带”的革命》的基础上修改而成,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名字的来历及其背景、寓意吧?
杨奎松:长期以来,我们的大学里一直有一门专门的中共党史课,是用来进行政治理论教育的。当年政治理论教育主要由三个部分所组成,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共党史。
哲学、政治经济学都自己的学科,中共党史既不算是历史,当时又已经废了政治学这个学科,不知怎的它就被划入了法学学科,中共党史系毕业的学生都拿的是法学学位,尽管一天法律也没有学过,一些人后来却可以拿着这个文凭摇身一变就成了律师。
因为中共党史在高校从来就不是当历史来讲,而是当政治理论来讲,高校党史教师当年自然也就习惯于照本宣科和以论带史的讲法,我在学校时就很不以为然。
从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毕业后接触到大量中共历史资料和各种相关的文献档案,1987年回到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任教时,就想着要给研究生开设一门专题课,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授中共的历史。
而那个时候,各种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教材汗牛充栋,但几乎所有的说法都有严格的规定,连措辞都不能有明显的不同,故版本虽多,大家却差不多全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基本上是你抄过来我抄过去。在那样一种情况下,我要在中共党史系里另讲一套中共党史,也没有可能性。
好在我当时在中外关系史教研室,这之前又比较系统地研究了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历史,因此我就开了一门中国现代对外关系史专题课,实际上专门讲中共革命的外部环境和原因。
这门课其实没有讲完,但讲稿写了一大半。
1991年恰好有个好朋友在中央党校出版社负点小责,我就乘机把这本书赶了出来,用了一个外行的人不大容易弄懂,因而也不会让人敏感的书名,顺利地把书印出来了。
但懂行的人也还是能够从它当时的副标题看出些门道来。当时的副标题是:“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因为当年没有人会从策略变化这种角度来考察中共革命历史上的成败,因此有些高校的老师还是很早就发现了这本书,并且也有不少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读过这本书。
只是,当年能看出门道的人太少,再加上出版社也不把这本书当回事,书出来后大概只售出去了不到1000本吧。也不知道后来超星图书网怎么找到这本书,也不通知我就把它电子化收到自己的书库里去了,不少读过它的学生多半都是从超星那里读到的电子版。

深度对话:有人通读了全书,认为这本书其实是民间版的中共党史,您怎么看?
杨奎松:这也是实话。我的这个选题和研究的角度,其实是有针对性的。当年,即1980年代,中共党史学界最流行,也是最政治正确的一个观点,就是“独立自主”说。
当时,有关共产国际当年帮助中共革命的各种史料大量涌现出来了,早先只讲中共党内斗争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传统讲法受到了挑战,于是就有了1935年遵义会议以前中共受共产国际领导干涉,因而革命接连失败,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坚持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因而革命节节成功的新说。
我从一开始就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我最早研究的使1935年以后的中共得以起死回生的政策转变,就明显是共产国际提出并且推动实现的。
此后进一步的研究,更证实了我的这种判断。实际上,任何弱国的革命,都和地缘政治的影响分不开;任何弱国成功的革命,更离不开背后大国的作用。
毛泽东的超人之处,并不在于他一贯正确,而在于他能够裹着意识形态的紧身衣,以利为先,游刃有余地利用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冲突,抓住历史机遇,居间获益。
所谓“中间地带”之说,既是用毛泽东自己的话,点明中国革命在大国政治中的地位;也是借以说明中共当年成功的秘诀,根本上就是利字当头,策略运用,不执于一端。这当然不会是官方说法,因此也只能算是民间的解读了。
深度对话:20年来为了完成新版著作(修改工作),你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原书只有36万字,新版补充进来了将近20万字,主要充实的是那部分的内容呢?
杨奎松:实际上,这本书当初赶得太急了,不仅最后少写了一节比较关键的内容,而且出版社的校对也出了不少错误,因此,书出之后我就想要修订了。
只是,十多年来一直很少有合适的机会能够再版和修订。这次修订,除了校正了许多印刷上的错误外,主要是补充了许多细节,并强化了对中共自身历史跌荡起伏的过程和原因的解读。
比如,中共苏维埃革命中的种种问题,中共历史上几度组织分裂的经过,苏联及共产国际援助中共的种种情况,以及抗战中和抗战后中共形势应对及其策略变动中的许多复杂因缘与巧合等。
2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已经有了很多新的资料发掘和史实解读上的突破,也不可避免地围绕着一些问题出现了激烈的争论。新版在这方面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并且回应了不同意见的质疑。
比如,曾有学者对抗战后苏联在东北向中共提供援助的规模和范围严重质疑,甚至不少著作和网友根本否认苏联有过实质性的援助,否认这种援助产生过实质性的作用。新版在这方面实事求是地做了正面回应,并在史料所及的范围内,例举了许多具体的史实。

深度对话:您自己对新书十分满意吗?您认为体制等方面的限制还会对您实事求是地撰写中共历史有所限制吗?如果有的话,您认为在哪些方面将不来可以做得更好些?
杨奎松:我在修订版前言里明确讲,我认为这本书是我的主要代表作之一。我之所以一直想要修订再版,也正是因为从我开始写这本书,到今天最终推出修订版,我始终相信这本书是我20多年来研究中共历史的一项总结性的成果。
20年前建立起来的这一突出强调地缘政治作用的解释框架,和着眼于中共阶级斗争思维逻辑与特点的解释路径,20年后依然如故。整个书的架构和观点,再版时没有做过任何修改。这也是我颇觉满意之处。熟悉历史研究的读者都了解,随着时间的不断后移,史料披露和发掘得也会越多。
因为大量新史料的出现,很多过去的研究,从史实到观点,都难免会受到冲击而不得不修正和改变。但是,我相信我的这本书经受住了时间的这一考验。
当然,中共历史中值得去讨论和研究的问题实在太多了,这本书只是从我自己认为最重要的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说明。即使是在我所梳理说明的范围内,也肯定还有理应实事求是地交待和分析的问题,这次没有能够去揭示和讨论。
但相比20年前,今天中共历史研究的政治环境已宽松许多了。我是“历史进化论”者,我相信看历史要着眼于历史长程,放眼几十年,人类社会短期内再折腾,总的趋势一定还是进步的。而且距离今天越远的事情,其政治敏感度就会越低,学术开放的程度也就会越高,这些年来我研究中共历史也是这样经历过来的。毕竟历史已经发生了,无论好坏,那都已经是事实,无可改变了。
后人知道这些事实,不过迟早而已。社会需要我们这些历史学家干什么?就是要我们运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和头脑,把历史真实的一面揭示出来,把杂乱无章的历史头绪理出一个比较清晰的线索来,让后人能够认清历史发展的主流,不会被神话或谎言蒙住了眼睛。
这种事总是要做的,今天做不到,明天;明天不行,还有后天。

深度对话:这本书着实很厚重,内容相当充实,但恐怕很多普通读者不能轻易读懂,您对这部分读者有什么好的建议?您对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有什么期待和寄语吗?
杨奎松:新版比旧版好多了,严格说来,这本书因为讲国际背景和解读意识形态、政策及策略变化较多,确实不如我其他专讲史实的书好读。虽然过去有些专业学者也读过旧版,但据我了解的情况,绝大多数人未必真的读懂了。
因此,新版在通俗性上做了较多的加工。一方面,增加了大量历史细节和故事;另一方面,加上了许多比较生动的小标题,而且每章都增加了一段小结。当然,即便如此也还是会有些读者感觉吃力。
我的建议是,如果读那些理论性较强的部分有困难,也不妨可以按照目录页上新增加的小标题,选读自己感兴趣的章节目。即使是这样读,相信对大多数关心中共历史的读者来说,也一定会有收获的。
不过,我想告诉年轻读者的是,历史的今天从来都是昨天的延续,两者是不可能割裂开来的。你要了解昨天的中共,了解它们何以失败,何以成功,就理当了解他们当年怎样想,怎样做,并了解他们为什么会那样想,那样做。
事实上,这本书目前的副标题叫“中共成功之道”,内容中更多地讲的却是它当年如何挫折、自残和失败的情况,是基于“失败是成绩之母”的逻辑,通过这种比较对照来论证解读它后来何以会成功的。
因此,任何想要了解或理解中共革命历史的读者是,就不妨读一下这本书。因为迄今为止,大概还没有第二本书可以提供给你这样一种认识中共革命的视角和比较系统的知识。

“我是一名历史学者,而不是党史学者”
深度对话:中共党史研究是公认的“敏感领域”,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杨奎松:这确是一个事实,因此迄今历史学界真正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学者少之又少。这是好事,也不是好事。
说是好事,是因为研究的人越少,致力这一研究的人就越容易出成果。说不是好事,是因为研究的人越少,成果的数量,包括成果的质量,也就难免越会受到局限,不容易提升得很快、很高。
深度对话:您从事该领域研究以来,研究规则发生过哪些重大的变化?什么时候扣得比较紧?现在的研究氛围如何?
杨奎松:我是1980年以后开始从事这方面的历史研究的。在此之前,中共党史研究不存在学术化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它完全是一个政治问题。我开始写论文的时候,中共党史研究已经开始和历史学研究发生密切关系了。
一是开始有了用历史学研究的方法来研究中共历史中个别史实的微观研究了;二是历史学的专业杂志开始接受符合相应的学术规范的中共历史研究的论文了。
我的第一篇论文,是研究共产国际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的作用的,就是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办的《近代史研究》杂志上的。
我是1982年进入中共中央党校的《党史研究》杂志做编辑的。5年编辑的经历,见识过不少所谓的“研究规则”,或称之为“研究禁令”。
最著名,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就是“两个决议”的限制。两个决议,指的是1944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至少有十几年的时间,相关部门或领导经常严令各研究机构或学术出版机关,凡涉及中共党史的文章与书籍,均必须严格遵守两个决议的口径,不得越雷池半步。
不过,这样的限制在1990年中期以后逐渐被突破了。这是因为,太多历史细节的研究完全不在两个决议规定口径的范围以内,相关部门根本无法把握。
与此同时,随着许多重大史实在资料发掘或研究上取得突破,传统的说法,包括决议中的说法,必须要有所修正。包括中共中央直属党史研究部门,也不能不突破决议口径的限制,修改诸如《毛泽东选集》中的相关注释和历史说明。
这种种修正和说法的改变,已经突破了决议的口径,自然也就使决议的限制逐渐形同虚设,无法一一对应地规定学者研究的口径了。
当然,中共党史至今也仍旧还是执政党用以宣传和教育的重要政治理论工具之一,因此,在一些可能涉及历史评价的重大问题上,它的研究限制依然很多。
好在今天历史学的众多研究者越来越关注于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他们的眼光越来越趋向社会基层,这使得今天研究中共历史的学者和同学,也都越来越远离过去那种高层政治史的研究领域,新的这类研究政治敏感度自然也就大大降低了。
深度对话:您一直不认为自己是一名党史学者,强调自己是一名历史学者,您认为两者的区别在哪儿?您赞成党史研究属于历史研究一个分支的观点吗?转行近代史研究对于您的党史研究有何帮助?
杨奎松:首先,我从来认为,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所谓“党史学”或“党史学者”。
“党”必须特指,或是共产党,或是国民党,或者别的什么党,不能因为今天中国实行一党制,“党”就变成了共产党的代名词。这不科学,也不正确,等于否认其他党存在,事实上不论民主党派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它们至少还是有自己的党名和组织,还在合法活动的吧。
其次,无论哪个党的历史,既然是历史,它就必然是人类社会整个大历史的一部分,对它的研究,自然也就注定了只能是一种历史研究。
因此,中共党史,准确地说应该称之为中共历史的研究,理当是历史研究无数对象中的一个。对中共党的思想、理论、组织、制度等等,当然可以不从历史的角度,而从不同学科的角度来进行其他专有的研究,但两者不可混为一谈,更不存在因为是执政党,就需要有一门专门为执政党设置的科学学科的逻辑和理由。
基于上述情况,我从不认为自己是所谓“党史学者”,也从不认为自己从事的是所谓“党史研究”。
我从来认为我是历史学工作者,我是在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在研究中共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其实并未转过行。
只是我原来在中共党史研究的部门工作过,后来进到历史研究教学的部门工作了而已。这只是工作单位的变化,而非我职业工作本身发生了变化。
当然,在不同的部门工作,工作的标准习惯和要求等也会不同。
从这个意义上,进到历史学科研究教育部门工作,对我在学术上走向规范和更加专业,帮助很大。

原文链接:http://news.qq.com/zt/2008/dialog/yks.htm | 


